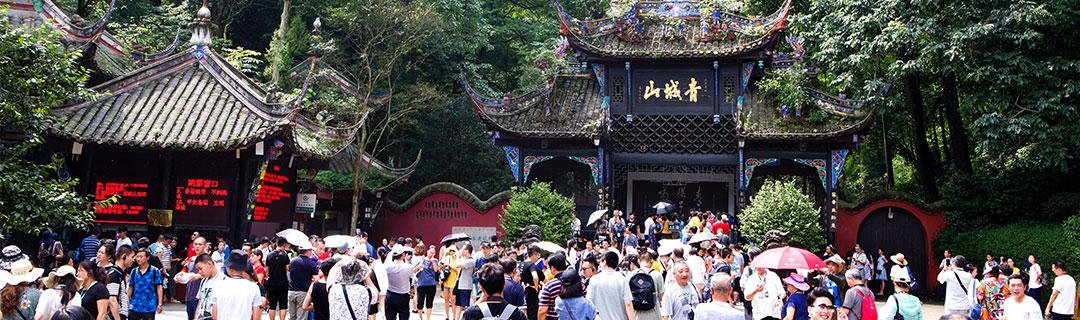[示范点]
持续的不法侵害因不法侵害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被短暂中断,但只要其主观上并未主动放弃,客观上仍具备继续实施不法侵害的条件,被侵害人在此情况下实施防卫行为,应认定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案号]
一审: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8刑初20号刑事判决书
二审: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刑终299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
公诉机关: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勇
被告人杨勇的妻弟刘勇与刘靖之间存在债务纠纷。2014年10月18日晚,刘靖因怀疑杨勇帮助其妻弟躲避债务,以找杨勇解决债务纠纷为由,邀约吴某某等多人在成都市成华区一环路东三段58号玉双苑小区杨勇住处附近蹲守。当杨勇驾驶川A9XH11奔驰越野车搭载同事简某某回到玉双苑小区门口时,刘靖上前拉杨勇车门让杨勇下车,杨勇见状迅速驾车离开。后杨勇驾车至成都市成华区万年场附近将其亲属刘健搭载上车,继续沿二环路行驶,刘靖等人分别驾驶两辆车一路追赶。当杨勇行驶至建设南二路沙河桥附近时,刘靖驾驶其中一辆川A234RE奔驰轿车超车后,将杨勇所驾车辆逼停;杨勇遂驾车绕开,继续行驶至建设南二路与建设南街交叉路口附近时,刘靖一方人员吴某某驾驶川AK98B3黑色丰田凯美瑞轿车,再次将杨勇所驾车辆逼停。后刘靖一方多人手持事先准备的棍棒陆续从所驾驶的奔驰轿车和凯美瑞轿车下车,截堵杨勇所驾车辆,并持棍棒用力打砸杨勇所驾车辆主副驾车窗玻璃等部位,致车辆受损、杨勇面部被碎玻璃划伤。尔后,根据天网监控视频显示,当晚23时26分40秒,杨勇驾车撞开横挡在其前方的凯美瑞轿车右侧;23时26分52秒左右,杨勇倒车后再向前行驶,此时刘靖一方人员登上凯美瑞轿车主驾位置,该车处于发动状态,另一人欲拉开该车副驾车门,其他部分人员手持棍棒走向凯美瑞轿车;23时27分02秒,杨勇驾车在前方掉头返回驶向凯美瑞轿车,其间有社会车辆横行,杨勇减速避让;23时27分04秒,杨勇驾车撞击凯美瑞轿车左前侧,将该车撞向路边大树下,致使该车左前门、车头等部位损坏。刘靖等人将凯美瑞轿车滞留现场,伙同其他人员驾驶另一奔驰轿车离开。
后经成都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价格鉴定复核意见,认定刘靖一方所驾驶的凯美瑞轿车因人为毁坏造成损失中等价格为人民币19688元。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杨勇与刘靖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协议,杨勇已支付刘靖赔偿款人民币35000元。2015年6月2日,刘靖因伙同他人打砸杨勇车辆被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向杨勇支付医疗费、车辆损失费等共计31780.1元。
[审判]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勇系脱离刘靖等人的截堵、打砸以后,报警之前,在极短的时间内主动掉头对停在现场的丰田凯美瑞轿车进行了撞击,明显具有主观故意,且当时刘靖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停止,故杨勇的行为不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杨勇故意驾车撞击他人车辆,造成对方财产损失19688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告人杨勇在审理过程中主动赔偿对方损失,酌定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以被告人杨勇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其拘役五个月零三日。
被告人杨勇上诉称,其返回撞击对方车辆时主观上没有毁坏财物的故意,也没有报复和泄愤的动机,不应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案发时,对方刘靖等人多次肆意逼停拦截上诉人车辆,并手持棍棒进行打砸,其撞击行为应构成正当防卫。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杨勇为了使本人及他人人身、财产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撞击不法侵害人车辆的手段制止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人财产利益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杨勇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首先,从起因上看,杨勇与刘靖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刘靖仅因怀疑杨勇帮助其妻弟刘勇躲避债务,即以找杨勇解决债务纠纷为由,纠集多人、事先准备棍棒在杨勇住处附近蹲守、驾车尾随追赶,途中两次截堵逼停,且在第二次逼停后组织多人持棍棒用力打砸杨勇所驾车辆车窗玻璃等部位,致车辆受损、杨勇面部受伤。刘靖一方借故寻衅,蹲守、追赶、逼停、暴力打砸车辆等一系列行为,不仅对杨勇的财产权益造成危害,也直接威胁到杨勇及其车上所乘坐人员的人身安全,明显属于不法侵害,且不法侵害客观存在;其次,从双方力量对比及现场情势来看,刘靖一方多人、驾驶两辆车,经追击、逼停,升级到多人下车同时持棍棒打砸杨勇车辆,不法侵害持续、紧急、激烈,而杨勇一直处于被侵害的危险之中;当杨勇驾车撞开横挡在其前方的凯美瑞轿车向前驶离,试图摆脱刘靖等多人的暴力打砸时,刘靖一方人员立即登上凯美瑞轿车主驾位置,车辆已处于发动状态,另一人准备登上副驾位置,其余部分人员手持棍棒走向凯美瑞轿车,持续的不法侵害系因杨勇冲出围堵而被迫暂时中断,但并未因刘靖等不法侵害人自动中止侵害或已被制伏、已丧失侵害能力等原因而结束,现实危险仍然紧迫,故不法侵害系正在进行;再次,从防卫意图来看,基于对持续侵害和累积危险的感受,杨勇为使本人或他人人身及财产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掉头返回撞击对方车辆的手段,以阻止对方继续实施侵害,其防卫意图明显;最后,从防卫对象和防卫限度来看,刘靖等多人所实施的不法侵害已危及杨勇等人人身及财产安全,而杨勇在紧急状态下选择撞击对方车辆,阻止对方继续追击实施侵害,且在撞击前对横行的其他社会车辆减速避让,防卫行为保持克制,其所实施的防卫手段没有超过必要限度,亦未造成重大财产损害。故被告人杨勇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正当防卫。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8刑初20号刑事判决,即被告人杨勇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拘役五个月零三日;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勇无罪。
[论证]
本案主要涉及如何认定正当防卫的问题。刑法理论上不乏对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研究,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的个体差异,分析案件的角度不同,是否认定正当防卫以及如何认定正当防卫,往往会引发很大争议,出现罪与非罪的根本性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杨勇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有以下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杨勇驾车撞开对方车辆脱离现场后,不法侵害已经停止,现实危险已经消除,其主动返回现场撞击对方车辆,属于有目的有计划、报复性地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应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杨勇在被对方一路围追堵截后,撞开对方车辆仅是暂时脱离危险,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其在短暂时间内返回现场撞击对方车辆,是为阻止对方继续对自己实施侵害,保护自己及车上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其行为应构成正当防卫。
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被告人杨勇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从前提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件、限度条件五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持续不法侵害的认定
从刑法规定来看,不法侵害的存在,是正当防卫得以行使的前提条件。不法侵害,应指广义上的违法,即违反国家法律和统一的法秩序,但不以违反刑法为限。换言之,刑法使用了“不法”一词,并未使用“犯罪”的概念,那么不法侵害应既包括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评价的侵害行为,也包括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一般违法行为。
持续不法侵害,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非法拘禁、绑架等继续犯以及非法侵入住宅、组织传销活动等侵害状态得以持续的不法形态,还包括攻击、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以持续的围殴等侵害形态。这里的持续侵害,就是持续危险,即“构成危险的状态具有较长的持续时间”的情形。在持续侵害状态中,不法行为的成立和既遂往往相对较早,但犯罪行为在较长时间内并未结束,在犯罪人彻底放弃犯罪之前,违法状态也一直持续,犯罪并未终了,在此过程中防卫人理应都可以防卫[ 周光权:《论持续侵害与正当防卫的关系》,载《法学》2017年第4期。]。对于持续进行的不法侵害,各个侵害行为之间相互连接。这种累积的系列侵害行为,对防卫人造成一种叠加的精神压力,评价时不能将各个时间点的不同行为分割评价,应以不法侵害行为开始为起点、彻底终了为终点,同时防卫人的最后反击行为,也应作为整体来评价。
本案中,杨勇与刘靖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刘靖仅单方面怀疑杨勇帮助其妻弟躲避债务,即以解决债务纠纷为由,纠集多人、事先准备棍棒,深夜在杨勇住处附近蹲守,在发现杨勇车辆后,拉车门让杨勇下车未果,即驾车一路尾随追赶,途中两次进行截堵逼停,且在第二次逼停后组织多人围堵并持棍棒用力打砸杨勇所驾车辆车窗玻璃等部位,致车辆受损、杨勇面部受伤。刘靖一方借故寻衅,蹲守、追赶、逼停、暴力打砸车辆等一系列行为,时间和空间上紧密衔接,从驾车跟随到下车截堵多人打砸,从一般不法侵害升级到暴力行为,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侵害的“量”不断增加,侵害的“质”发生改变,危险程度持续升级,不法侵害不仅损害杨勇的财产权益,也直接威胁到杨勇及其车上所乘坐人员的人身安全,明显属于不法侵害,不法侵害客观存在、且处于累积升级的持续状态,符合正当防卫的前提要件。
从本案案情总结分析,借故在他人家附近蹲守、一路紧追、两次逼停后围堵打砸车辆,应认定为存在持续的不法侵害。
二、关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认定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关于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刑法理论上有进入侵害现场说、着手说、直接面临说与综合说等,我们认为应根据具体案件具体判断。本案中不法侵害人深夜在杨勇住宅附近蹲守,在等到杨勇车辆到家附近时上前拉车门要求杨勇下车时,其借故寻衅、骚扰他人生活安宁的不法侵害状态已经开始。关于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刑法理论上也有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排除了不法侵害的客观危险就是结束时间;也有观点认为不法侵害被制止就是结束时间。我们认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应是指不法侵害已经不可能继续侵害或者威胁他人的合法权益,主要表现为不法侵害人已被制服、已丧失侵害能力、已自动中止侵害、已自动逃离现场等情形。对于持续的不法侵害,在防卫人采取防卫手段阻止侵害继续进行时,持续的状态因不法侵害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暂时中断,但其主观上并未中止或放弃实施侵害,客观上亦具备随时继续实施侵害的条件,甚至已经着手实施继续侵害的准备,则应当将不法侵害认定为正在进行。不能脱离当时的现场情势、双方力量对比和防卫人叠加的危险感受,武断地得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结论,并依此将防卫行为纳入犯罪视野进行评价。如不允许行为人基于现实的危险预测进行防卫,就等于变相剥夺其正当防卫权;如要求必须受到实际侵害才能进行防卫,本就处于劣势的行为人将会完全丧失防卫能力,或遭受更加严重的侵害后果。
如何认定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结合本案,我们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应整体关注案件发展的全过程,不能孤立看待防卫瞬间的行为。本案中,对方的不法侵害并非偶发、短暂的,而是蓄意、持续累积存在的。从不法侵害的强度、缓急、性质,及双方力量对比来看,刘靖一方从多人、驾驶两辆车追击、逼停,升级到多人下车同时持棍棒打砸杨勇车辆,不法侵害从未停止,其暴力程度持续增强、且紧急而激烈,而杨勇一直处于劣势,多次避让却仍处于被侵害的现实危险之中。其次,应全面考量现场情势因素,不能忽视不法侵害的延续状态。本案中,对方的不法侵害并不是一种或放弃或继续的两可并存的状态,而是已开始着手继续实施的紧迫状态,且无论从任何角度都无法得出不法侵害已经终止的唯一结论,从整体过程来看,也与之前的不法侵害在时间、空间上紧密相连,应认为侵害处于延续状态。具体而言,当杨勇驾车撞开横挡在其前方的凯美瑞轿车向前驶离,试图摆脱刘靖等多人的暴力打砸时,刘靖一方人员立即登上凯美瑞轿车主驾位置,车辆已处于发动状态,另一人准备登上副驾位置,其余部分人员手持棍棒走向凯美瑞轿车,另一辆车就停在旁边也具备随时延续之前追击状态的条件。持续的不法侵害系因杨勇冲出围堵而被迫暂时中断,但并未因刘靖等不法侵害人自动中止侵害或已被制伏、已丧失侵害能力等原因而结束,现实危险仍然紧迫存在。最后,应设身处地考虑防卫人对于持续侵害累积危险的现实感受。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结束的认定,不能脱离整体过程来评价,更不能忽略被告人在当时所处的高度紧张和恐惧叠加的状态下对现实危险的心理感受。即便是以理性第三人的标准来判断,也不能不考虑行为人此时此刻的累积的危险感受。综上,持续的不法侵害状态,即使从表面上看在防卫瞬间不法侵害停止,但从整体看侵害行为正在进行时,仍然可以进行防卫。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不仅要看客观上现实危险是否存在,也要考虑行为时防卫人对于不法侵害状态的主观认识。
因此,持续的不法侵害表面上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被短暂中断,但只要不法侵害人主观上并未主动放弃或逃离,客观上仍有可能继续实施不法侵害,则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应认定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三、关于防卫意识的认定
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具有防卫意识(即具备了主观的合法性要素),才能成立正当防卫。防卫意识,包括防卫认识与防卫意志。防卫认识,是指防卫人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意志,是指防卫人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目的。但防卫意识的重点在于防卫认识,换言之,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相对抗,就应认为具有防卫意识[ 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
本案审理中,有意见认为杨勇驾车已脱离现场,对方不法侵害虽不能排除可能继续,但仅是一种“可能性”,不能直接等同于“正在进行”;且依据常人思维,杨勇既然已经脱离现场,应选择加速驶离,或到就近公安机关寻求保护,而其却选择主动返回撞击对方,其主观方面并非意在制止不法侵害,其行为带有明显的报复性质。我们认为,当杨勇面临持续紧急的不法侵害,采取掉头返回撞击对方车辆的手段阻止对方继续实施侵害,在内心叠加的高度惊慌和恐惧下,任何人的主观心态都必定是复杂的,但只要主观上存在阻止、对抗不法侵害的动机和目的,即可以认定符合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至于是否有愤怒、报复的心态,不影响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
概言之,防卫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在与不法侵害相对抗,其具备对抗、阻止不法侵害的动机和目的,即认定存在防卫意识。至于是否存在报复心态,不影响防卫意图的认定。
四、关于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正当防卫中排除不法侵害,要求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通常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针对不法侵害人人身进行防卫,如束缚不法侵害人的身体、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二是针对不法侵害人的财产进行防卫,如不法侵害人使用自己的财产作为犯罪工具或者手段时,如果能够起到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的作用,也可以通过毁损财产进行正当防卫。
本案审理中,有意见认为,杨勇返回撞击对方车辆的行为不仅仅是针对车辆,其对于撞击行为可能造成对方车上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危害也是持放任心态,如果撞到对方的人,势必要承担严重的后果,构成更严重的犯罪。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是从结果切入来反推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这样的思维逻辑容易引起正当防卫认定上的偏差。那么,即便从后果来反推,客观上也并未造成对方人员受伤的实际后果;从主观上更无法认定杨勇是针对对方人员实施撞击行为,打砸时对方多人均下车参与,且在杨勇冲出现场后短暂数秒内,其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与现场相背行驶,是无法确定对方人员是否已经上车,更无法了解天网监控所全面显示的对方人员再次准备上车、聚集,可能继续追击的状态,其返回撞击行为类似于丛林状况下的应急反应,动机就是要阻止对方继续实施侵害,选择撞击对方一直追击自己的车辆,毁损对方继续侵害自己的工具。杨勇所选择的防卫对象,并没有针对对方站在路边的人员,而为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针对对方车辆进行撞击,且在撞击前对横行的其他社会车辆减速避让,防卫行为保持克制,并没有侵害更严重的权益。
总之,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防卫,既包括对其人身进行防卫,也包括对其财产进行防卫,通过损毁作为工具或手段的财产达到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符合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五、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必要限度”,是指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的合理需要为标准,且刑法放宽了限制,只要不是“明显”超过即可。具体判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看不法侵害的强度、侵害的手段、对方人员的多少和强弱、现场的情势因素,也要权衡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法益和所攻击的法益之间的利益对比。
本案中,杨勇面对对方蹲守、追击、逼停、打砸一直逃离避让,对方的侵害行为一直持续;在杨勇在返回撞击前,途中遇到其他社会车辆进行了避让,也表明其并非出于不管不顾的报复心态,防卫行为相对克制。从防卫限度来看,刘靖等多人所实施的不法侵害已危及杨勇等人人身及财产安全,而杨勇在在警察尚未到达现场,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情形下,针对对方车辆进行撞击,阻止或震慑对方继续追击实施侵害,其所实施的防卫手段没有超过必要限度,损害后果上亦未造成重大财产损害。杨勇选择撞击对方车辆的手段,应是适当、可选择的防卫方法中最轻的,也就是说其在实现防卫效果的前提下采取了能选择的最轻的防卫手段。在当时仓促紧张的情形下,不应对杨勇的行为过于苛求,不能要求其克制、理性的等待公权力的救济,即继续选择躲藏逃避,或寻找其他更适当更周全的防卫手段。在利益平衡上,其所保护的人身权益高于对方的财产权益损害,且后果上仅仅是财产损害,且并未达到重大程度,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换言之,我国刑法并未要求正当防卫必须要穷尽一切手段后才能实施,相反,即使其有条件躲避或者求助公安机关,仍然有权实施正当防卫。防卫人的防卫行为保持克制,没有超过必要限度,也未造成重大财产损害,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本案中二审法院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符合刑法立法精神,通过司法裁判向社会明确传递鼓励正当防卫的信号,鼓励公民及时进行正当防卫,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彰显法律的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于社会价值导向的引领作用,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编写人: 陈娜
案例论证人: 陈娜